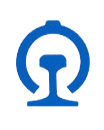凌晨的铺轨工区宿舍,万籁俱寂,唯有窗棂上那道熟悉的剪影,总在不经意间闯入视线 —— 是张工。他总爱披着那件洗得发白、边角磨出毛边的工装外套,就着一盏暖黄的台灯,在纸上写写画画。笔尖划过纸面的 “沙沙” 声,轻得像风拂过麦田,又像铁轨与车轮相遇时的温柔私语,在寂静的夜里,格外安心。
三年前,我还是个刚走出校园、握着水准仪手都发颤的新手。面对眼前陌生的仪器、延伸向远方的钢轨,满心都是手足无措。就在我盯着仪表盘发呆时,一双粗糙却温暖的手覆了上来,轻轻稳住我发抖的手指。“别慌,记住口诀:调平瞄准读数亮,误差控制最关键。前后视线均等平,一站数据随时录。仪器平放少偏撂,脚架撑稳硬地基。”
张工的声音带着晋北人特有的爽朗,尾音微微上扬,像清晨铁轨尽头那抹慢慢亮起来的晨光,驱散了我所有的紧张。那天,我们沿着刚铺好的钢轨,一步一步走了七公里。他蹲下身,指着轨枕上的编号,一字一句地说:“这是每块轨枕的‘身份证’,哪块在哪个位置、有什么特点,都得记牢,就像记住朋友的生日一样。” 阳光洒在他鬓角的白发上,我忽然明白,所谓匠心,就是把每一个细节都装进心里。
盛夏的隧道里,温度直逼 40℃,混凝土搅拌机的轰鸣震得人耳膜发疼,空气里满是粉尘和热浪。一次施工时,张工突然把自己的安全帽摘下来,扣在我头上。我低头时,瞥见他后颈的皮肤 —— 那是被烈日反复暴晒后脱了皮的模样,一道道纹路像干涸的河床,触目惊心。“小同志,记着,隧道施工就像姑娘家绣花,一针一线都马虎不得,差一点,后续都可能出大问题。”
他蹲在刚初凝的混凝土前,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小锤,轻轻敲击着表面。“咚咚” 的声响在隧道拱顶下回荡,竟生出一种奇妙的韵律。那一刻,我第一次觉得,那些冰冷的钢筋、水泥、钢轨,不是没有生命的建材,而是能在匠心打磨下,谱出动人乐章的 “音符”。
还记得那年盛夏,公司要举办建党百年主题演讲比赛。我熬了好几个通宵写的演讲稿,被张工用红笔改得密密麻麻。“这里得加细节,光说大道理不行。” 他翻出一本泛黄的工程日志,封皮上还沾着淡淡的灰尘,“你看,当年我们修敦格铁路,零下十几度的天,钢轨焊接口怕冻,得用棉被裹着保温,夜里还得轮流守着,就怕出一点差错。”
我凑过去看,泛潮的纸页上,还留着当年当金山的雪粒印记,字迹却依旧工整有力。后来,我的演讲《钢轨延展信仰 温度传递力量》拿了二等奖,颁奖词里那句 “让冰冷的铁轨有了人性的温度”,我知道,这不是我的功劳,而是张工用数十年的坚守,教给我的最珍贵的东西 —— 铁路人的心,永远和钢轨一样,炽热而坚定。
今年开春,张工把他视作 “宝贝” 的全站仪,郑重地交到了我手里。那台仪器外壳有些磨损,却被擦拭得一尘不染。“当年我师傅把水准仪传给我时,说‘仪器在,标准就在’,现在我把它传给你,记住,测量员是工程的眼睛,眼里容不得半粒砂砾。” 他擦拭镜片的动作,轻得像在抚摸初生的婴儿,眼神里满是郑重。
如今每次架设仪器,我总会想起他教我的口诀:“先设站,后定向,操作简单不要慌。” 想起他蹲在钢轨旁,认真核对每一个数据的模样;想起他说 “轨枕是铁轨的身份证” 时,眼里的光。
前些天整理库房,我在铁柜最上层,发现了张工的一摞工程笔记。从几十年前手绘的工程图纸,到近些年打印的智能建造方案,一页页泛黄的纸页,记录着他走过的每一段铁轨,熬过的每一个夜晚。
铁轨向远方延伸时,总会留下清晰的辙印;而在这条永无止境的筑路征程上,匠心也在一代代人手中传递。从前,是张工牵着我的手,教我认识钢轨、读懂匠心;如今,我也想沿着他走过的路,把这份热爱与坚守,写进属于我们这代人的轨道诗行里。